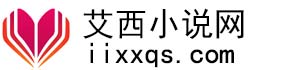50-60(14/24)
一块糕点,小心地递给对方:“很好吃的。”这个年纪的少年人,无论吃多少都嫌不够。
同桌接过糕点,正准备道谢,却见跟随在小皇帝身边的宦官捏一本奏疏,站在门口,时不时探头过来。
“有事?”纪淮舟停了动作。
阚英立刻小跑着进来,颤颤巍巍地跪下,双手将奏折捧上:“陛下、陛下请看……”
难得见阚英这么诚惶诚恐的样子……
纪淮舟接过奏折,首先认出其上的字,是东门亭的笔迹,这些日子少臣二人时常通信,因此他很熟悉对方的字。
本以为是寿昌伯那件事的后续,没想到内容截然相反,剑指会试。
“……历岁会试,西宁府无上榜者,今年亦如之。①”
纪淮舟反应了一会,才意识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
捏着奏折的手逐渐用力,最后拍在案上,他眼睛灼亮,似有火焰燃烧,咬牙切齿道:“回宫!”
同桌小心捧着那块点心,呆呆地看着对方离开的背影。
“昀达兄?”其他试课的学子见他发呆,多问了一句。
“没事。”那学子回忆起纪淮舟纪亮的目光,心却在一下一下地震响。
纪淮舟懵了一会儿,方才后知后觉地记起,人昨夜便被自己差回宁州去了。
他支着身子起来时脑袋一阵眩晕,只好按着眉心缓解,昨夜记忆似是被人抹去一般,米酒走后他做了什么来着?
做了什么不记得,可再不润润嗓,喉咙真要被灼穿了。
纪淮舟跌跌撞撞地起来,只觉得一阵头重脚轻,颠三倒四地走到桌边端起茶盏时,忽的定住了。
一只狼毫,此刻正服服帖帖地摆在桌上,纪淮舟一口气饮尽了隔夜冷茶,抓起那笔看了又看,错不了,正是纪涟的。
他想起来了,昨夜似是寻不见此物,又想起些陈年旧事,迷迷糊糊缩在门口睡着了那怎的今早醒来是在床上!
纪淮舟静默片刻,心下已然猜得七七八八,他身上还有些热,应是昨夜吹了许久冷风,又着了凉。
霍少闻昨日刚同他打了一场,应是讨厌透了他,心上人的东西被他捡着了,还回来作甚?
纪淮舟想不通,也不愿再想,许多事等着他去做,眼下夫立轩那头就得尽快挑个时间去拜会,距离冬祭只有半月了。
他面色倦沉地揉着耳根,一阵虚恍,心下有一搭没一搭地想着事情。
煊都着实不是个好地方,这地儿大抵克他,做什么事都像被绊着手脚,得分外小心,才不至于原形毕露。
房门突然被叩响了。
窗外辽阔长空传来猛禽的唳叫,纪淮舟在这动静里披上件外衣,没事人一样把这杆狼毫揣进怀里,深吸口气,藏住疲惫的困意,露出点掺假的笑意,大步开了房门。
门口仅立着一人,幸好不是霍少闻。
老府医微埋着头行完礼,便进门给纪淮舟搭脉问诊,不多时一躬身,道:“夫郎应是染了风寒,并不严重,按时服药,注意保暖即可。”
纪淮舟应了声,这府医刚要退下,忽然又被叫住了。
“谁叫你来的,”纪淮舟问,“小将军吗?”
老府医赶紧作揖:“是。”他顿了顿,又急急抬头补充道:“将军对夫郎很是关切,一大早便差我来此候着。夫郎只待静养几日,病好即可再度同房。”
“好啊。”纪淮舟皮笑肉不笑,抬手捞起满头乌发,露出修长脖颈,这颈子上的几指红印还余淡痕,一路延伸到衣领之中,像是半遮半掩酿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