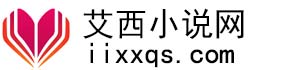40-47(25/53)
,绝不容许她反驳。挂上电话,喻礼所有关于情爱的心都消散了,她依旧没搭理程濯,裹上薄被睡觉。
在她闭上眼之后,她听到有人关掉壁灯,轻轻躺在她旁边。
他的气息淡雅却有侵略性。
喻礼忍不住往一旁缩了缩身体。
月色朦胧透过纱窗,她很快有了困意。
半睡半醒之际,听到寂静的夜里,传来一道清润的声音,“我没有让二公子伤得很重。”
喻礼以为是梦,直到他又执着重复一遍。
喻礼眉心蹙起来,她当然知道!那只是喻济时的说辞,伤重伤轻,不过是他喻济时一句话的事情!
她翻了个身,直视他,不悦道:“你是没话找话吗?大半夜解释这么愚蠢的问题!”打扰她睡觉!
程濯勾了下唇,身体往她这边倾了倾。
他伸手去抚她柔软的发,垂眸看她因怒气而明亮的眼睛,“你还没有告诉我,我们的冷战什么时候结束。我担心你一直不理我,只好问个愚蠢的问题吸引你的注意。”
喻礼没思考过这个问题。
她很少有真正生气的时候,她的生活也不容许她长久将郁气长久储在心里——除非她不想活了。
“我不知道什么冷战结束,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,就莫名其妙和好了。”
她从不因为这些事感到煎熬,自然不知道,有人会因为跟她冷战这件事黯然神伤,夜不能寐。
程濯问:“那你现在,还想跟我结婚吗?”
喻礼沉吟片刻,冷静道:“不想了。”
她不喜欢强人所难。
她太富有,对任何事情都不抱有执念。
感受到他呼吸发沉,她瞥他一眼——即使什么都看不见。
她慢悠悠补上一句话,道:“即使你现在想跟我分手,我也会从容放手,我这个人很擅长好聚好散。”
程濯呼吸彻底静下来,昏暗中,喻礼看不清他神色,只感觉他扣着她后脑的手越扣越紧。
她无声勾了勾唇。
程濯彻底将她扣在怀里,半晌,他静静道:“我很不擅长好聚好散,尤其是跟你的好聚好散。”
他说:“喻礼,你要跟我结婚这件事,我当真了,我们回国就准备。”
喻礼忍不住“哼”了一声,伸腿踹他一脚,“你想结就结?
而且你这是什么语气,皇上下旨的语气!我是不是该说一句谢主隆恩?”
程濯原本压抑的心境又被她弄得松缓,他失笑,额头抵在她面上,心情变得很好。
“是不该这样讲。”
他轻声细语,学着宫廷剧的语调,说:“奴才求殿下跟奴才成婚,如果殿下愿意,奴才一生一世感念殿下的恩德。”
他这样清润的好嗓子一本正经说这样话,说不出的怪异,喻礼在他怀里笑得花枝乱颤,“我只听过宦官是自称奴才的,你怎么也自称奴才?”
程濯并不恼她这样的戏谑,“我是不是,你不是最清楚吗?”他吻她敏感的耳尖,声音越发低柔,“殿下要不要奴才伺候?”
喻礼点了点下颌,骄矜道:“可。”
他伺候得太好,喻礼上飞机后困倦得扣上眼罩睡觉。
温婧拿着轻薄柔软的毯子,打算替喻礼盖上,手还没有伸过去,一只修长如玉的手便抬起,拿过暗红色羊绒毯,轻轻替喻礼盖上。
温婧坐回自己的座位,暗瞟一眼清隽如玉,霁月清风的男人,在工作群里发,[复宠了。]